期货故事之雷曼倒塌:火箭科学家之“功”与“过”
发布时间:2021-1-13 15:29阅读:745
雷曼倒塌:火箭科学家之“功”与“过”
这是一个场外金融衍生品的故事。
雷曼倒了!2008年9月15日,这家有158年历史,以债券和债券衍生品交易为主要业务的美国第四大投行申请破产,成为美国金融史上最大的金融机构倒闭案。雷曼倒在巨额的场外金融衍生品交易上。华尔街人士分析说,“雷曼自身的一系列自埋苦种和市场不允许其喘息的步步紧逼:次级和次优级贷款及债券严重缺乏流动性,巨额缩水的商业不动产及贷款债券存货堆积如山,对冲失效,盯市会计准则如紧箍咒,信用违约互换(CDS)如鬼手掐着雷曼的脖子走”。  雷曼挺不住倒下了。
雷曼挺不住倒下了。
雷曼公司的破产,揭开了2008年金融大海啸的序幕。以后,许多人一提起“雷曼”这个名字,就会联想到场外金融衍生品,因为它过度交易了场外金融衍生品而导致破产。谈到场外金融衍生品,不能不提“金融工程”这个来自西方的词语。这是一门利用信息技术和数理知识,建立模型,进行金融产品设计的金融专业技术。这门课的开设,在美国等西方大学里也是最近不到30年的事。我常听身边一些朋友谈起大学里这个专业很抢手,许多朋友的子女都有志于这个专业,要挤进去不容易。这显然受到美国金融衍生品市场火爆的影响。1929—1933年美国大危机后,随着美国实体经济的大发展,金融业分业经营的进行,银行等金融机构非常关心自己内部不断积累的风险如何消化,为改善自己的风险管理冥思苦想。到20世纪70年代末,金融机构利用金融工程的创新活动,使它们有办法将金融风险从基础资产中剥离出来,设计成新的金融产品作为独立的商品进行买卖。这一技术方便了一些不愿意持有风险的金融机构把风险卖出去。金融工程是通过实施金融创新来找到对特定财务问题更好的解决方案,它开始于对问题的诊断,对可能方案(可能是一种新的金融工具)的分析,新工具的产生、定价,与多个客户相关的个性化解决方案。金融工程,可以识别、剥离基础资产中的任何风险,然后通过对基础资产归类、重组、切割、评估、保险、定价,并单独作为商品进行交易。
1997年底,J. P.摩根公司推出了一套近100亿美元的信用衍生产品,又称BISTRO(broad index synthetic trust offering),它将自己资产簿上的100亿美元的贷款囊括起来,重组包装,切割成好几块,每块具有不同的信用风险。然后,再将各块信用风险卖给其他银行或金融机构。通过这种途径,即便原先的贷款仍在摩根的资产簿上,但信用风险已经从摩根银行转嫁到了其他金融机构。信用衍生产品是J. P.摩根公司开天辟地的一大创举,是对金融领域的一大贡献。  信用衍生产品是资产证券化的一种形式,将原先静静地躺在银行资产簿上的贷款变成证券加以出售,把间接金融的产品变成了直接金融的产品。通过信用衍生产品,银行同公司的业务关系依然如故,贷款仍在银行的资产簿上,但银行却转手把贷款的风险给卖掉了,以减轻自身的负荷。这一出售过程可以是匿名的,即公司并不知道它在某银行的贷款已经被转让,信用衍生产品的投资者也不知道投资的相关资产具体是哪家公司的,只知道是哪个行业、信贷评级是多少。这样银行避重就轻,保留了有盈利的流程业务,减少了无盈利或盈利少的资产项目。这样的创新对于银行转移和分散风险是有利的,但过度了也会贻害无穷。
信用衍生产品是资产证券化的一种形式,将原先静静地躺在银行资产簿上的贷款变成证券加以出售,把间接金融的产品变成了直接金融的产品。通过信用衍生产品,银行同公司的业务关系依然如故,贷款仍在银行的资产簿上,但银行却转手把贷款的风险给卖掉了,以减轻自身的负荷。这一出售过程可以是匿名的,即公司并不知道它在某银行的贷款已经被转让,信用衍生产品的投资者也不知道投资的相关资产具体是哪家公司的,只知道是哪个行业、信贷评级是多少。这样银行避重就轻,保留了有盈利的流程业务,减少了无盈利或盈利少的资产项目。这样的创新对于银行转移和分散风险是有利的,但过度了也会贻害无穷。
也是这一年,摩根士丹利的一位叫弗兰克·帕特诺伊(Frank Partnoy)的场外衍生品交易员写了一本叫《泥鸽靶》  的书,讲述了他在离开摩根士丹利之前,所了解的投资银行设计和销售衍生品的一些细节。因为这本书,他还同摩根士丹利打了一场为时不短的官司。他在书中写道,由于场外衍生品大行其道,在华尔街的激励机制下,新产品创新层出不穷,日日更新,卖得很好,成为投资银行和商业银行新的利润增长点。很多学数学的、学工科的高才生和教授从哈佛、斯坦福、普林斯顿、麻省理工等名校来到华尔街,利用金融工程技术为金融机构进行场外衍生品模型设计和产品销售。美国畅销书作家刘易斯在《大空头》一书里也说,华尔街激励机制的不合理是导致金融危机爆发的因素之一。由于金融衍生品的销售、交易情况和销售人员、交易员的当期业绩挂钩,推销的产品越多、交易量越大,他们年底的奖金就越多。即使公司亏损,原来签订的奖金协议还是要兑现的。这种激励机制导致销售人员或交易员肆无忌惮地开发和推销产品。刘易斯曾经的老板,以债券交易闻名华尔街的所罗门兄弟公司首席执行官(CEO),1986年在搞垮公司的同时,却拿走了合同约定的300多万美元奖金。2006年,摩根士丹利的一名交易员在一笔次级抵押贷款债券交易中亏损90亿美元,被扫地出门时居然还拿到3000多万美元的奖金。一位名不见经传的纽约对冲基金经理保尔森,为他的投资者赚了大约200亿美元,他自己则赚了将近40亿美元,主要就是通过债券衍生品对赌花旗集团及其他大投行的次级抵押贷款债券而赚到的。刘易斯感慨道:“天文数字般的红利,看不到尽头的流氓交易员队伍,带来一个又一个的风险,但华尔街大银行依然保持着增长势头,同时增长的还有它们支付给那些从事没有任何社会效益的工作的26岁年轻人的薪水。”华尔街这种不正常的激励机制不仅导致金融严重脱离实体经济,也带来高端人力资源错配。许多一流教授学者、科技人才流向华尔街去设计、销售谁都看不懂的金融衍生品,然后把风险转移、放大到股票市场、货币市场、实体经济,从而引发了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并席卷全球。在《泥鸽靶》里,帕特诺伊称这些人为“火箭科学家”。
的书,讲述了他在离开摩根士丹利之前,所了解的投资银行设计和销售衍生品的一些细节。因为这本书,他还同摩根士丹利打了一场为时不短的官司。他在书中写道,由于场外衍生品大行其道,在华尔街的激励机制下,新产品创新层出不穷,日日更新,卖得很好,成为投资银行和商业银行新的利润增长点。很多学数学的、学工科的高才生和教授从哈佛、斯坦福、普林斯顿、麻省理工等名校来到华尔街,利用金融工程技术为金融机构进行场外衍生品模型设计和产品销售。美国畅销书作家刘易斯在《大空头》一书里也说,华尔街激励机制的不合理是导致金融危机爆发的因素之一。由于金融衍生品的销售、交易情况和销售人员、交易员的当期业绩挂钩,推销的产品越多、交易量越大,他们年底的奖金就越多。即使公司亏损,原来签订的奖金协议还是要兑现的。这种激励机制导致销售人员或交易员肆无忌惮地开发和推销产品。刘易斯曾经的老板,以债券交易闻名华尔街的所罗门兄弟公司首席执行官(CEO),1986年在搞垮公司的同时,却拿走了合同约定的300多万美元奖金。2006年,摩根士丹利的一名交易员在一笔次级抵押贷款债券交易中亏损90亿美元,被扫地出门时居然还拿到3000多万美元的奖金。一位名不见经传的纽约对冲基金经理保尔森,为他的投资者赚了大约200亿美元,他自己则赚了将近40亿美元,主要就是通过债券衍生品对赌花旗集团及其他大投行的次级抵押贷款债券而赚到的。刘易斯感慨道:“天文数字般的红利,看不到尽头的流氓交易员队伍,带来一个又一个的风险,但华尔街大银行依然保持着增长势头,同时增长的还有它们支付给那些从事没有任何社会效益的工作的26岁年轻人的薪水。”华尔街这种不正常的激励机制不仅导致金融严重脱离实体经济,也带来高端人力资源错配。许多一流教授学者、科技人才流向华尔街去设计、销售谁都看不懂的金融衍生品,然后把风险转移、放大到股票市场、货币市场、实体经济,从而引发了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并席卷全球。在《泥鸽靶》里,帕特诺伊称这些人为“火箭科学家”。
当然,信用违约互换市场也是需要的,利用它转移和管理金融机构的风险是必要的。危机中出的问题主要是“火箭科学家”把次级贷款作为基础资产来设计衍生品,经过几道衍生,到了信用违约互换这个产品上,已经经过几轮转手,前方基础资产的风险无人知晓。许多基础资产质量低劣,风险巨大。在华尔街投行的贪婪、评级公司的逐利和失责、监管的真空等多种条件的激励下,“火箭科学家”设计的这些复杂衍生品大行其道并泛滥成灾。如果“火箭科学家”设计的衍生品以服务实体经济为目的,这是经济发展需要的。但这些场外衍生品的创新与销售主要是为金融机构的利润考虑,急功近利,“脱实向虚”,偏离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方向,搞了很多除设计者外其他人根本看不懂的东西,蒙蔽投资者,获取暴利。
衍生品的风险大小,与其作为设计标的的基础资产关系极大。金融危机中出问题的衍生品,大多是以次级贷款作为基础资产的产品。比如,导致雷曼破产的因素之一的金融衍生产品即是如此。刘易斯在《大空头》中揭露了这个产品从选择基础资产开始,最后是如何成为金融衍生品的。刘易斯说,次级抵押贷款债券、次级贷款担保债务权证(CDO)、信用违约互换等场外金融衍生品的交易量在21世纪最初几年里疯狂增长。它们都是建立在次级抵押贷款这个基础资产上的,助推了次级抵押贷款市场的疯狂。在美国,房屋抵押贷款最初只是对有偿债能力的美国购房人开放,后来扩展到了偿债能力较差的美国人甚至没有稳定收入的移民购房人。抵押贷款债券是利用金融工程技术对抵押贷款进行资产证券化处理后产生的债券,它是一种对来自一个由数千笔单独的住房抵押贷款组成的池子里现金流的追索权。而次级抵押贷款债券就是指池子里的都是信用度极低、可能收不回来的贷款。如果能够把这部分贷款卖出去,风险就转移到买者手上,贷款银行就可以高枕无忧了。金融创新使得不愿长期持有次级抵押贷款资产的银行,将次级贷款资产卖给投资银行,后者买入后进行资产证券化处理,设计成债券进行买卖,赚取佣金收入或价差收入。这样负债就转到投资人手上,银行有了新的资金来源,可以继续发放新贷款,并转手把新贷款卖出。如此这般反复循环,银行贷款资产形成的债券越来越多,杠杆越来越高,市场越来越大。“火箭科学家”的创新活动让越来越多的负债变成可交易的债券及其衍生品,可以向任何人销售。银行觉得贷款风险转移出去了,因而对贷款对象的信用要求放松,道德风险由此而生。如果这项创新发生在《大空头》书中所言的,美国人中有偿债能力的那部分人中间,它是有利于金融机构提高效率的,风险应该是可控的。问题在于,商业银行和贷款公司把这类称为次级贷款的资产转卖给了投资银行等金融机构,进行资产证券化并成为新的债券后,最初的风险源在所谓的“金融创新”活动中模糊了。《大空头》中有好几个例子:一个年收入14000美元的采摘草莓的墨西哥人,在身无分文的情况下用银行抵押贷款购买了一套价值72.4万美元的房子;一位来自牙买加的保姆,一家贷款公司向她提供零首付浮动利率抵押贷款,在零首付获得第一套房屋后,她利用这套房屋和后来购买的房屋向金融机构反复抵押融资,一下子在纽约买了5套房子。他们都是不具备还款能力的人。银行和贷款公司不管他们能否还款,因为发放的次级贷款能够很快卖给投资银行,然后利用新获得的资金再向不具备条件的人放款赚钱。次级贷款市场成为新的抵押债券的来源。《大空头》中的人物,证券分析师艾斯曼说“华尔街卖出的东西什么都不是”,只要买房者一断供,发放次级抵押贷款的金融机构、承销发行次级抵押贷款债券的投资银行、交易次级抵押贷款债券衍生品的金融机构就会出现大问题。
和雷曼一起受世人关注的还有美国国际集团(AIG),由于持有了太多的信用违约互换,它紧步雷曼后尘,也濒临破产边缘,要不是美国政府出手,它也会葬身于金融海啸。信用违约互换实际上就是一份保单。当初这个产品产生时是作为一种保值工具,每6个月支付一次保费,条款固定,主要是针对投资者购买如通用电气公司等大企业发行的长期债券而设计的保险产品。该产品由J. P.摩根公司发明,由美国国际集团销售,为银行贷款或企业债券进行保险。21世纪初的前几年,华尔街还没有针对次级抵押贷款债券的信用违约互换产品。后来,市场上先知先觉的精明者发现了次级抵押贷款债券的巨大风险,一旦房地产市场崩溃,介入这个市场的公司肯定会遭受巨额亏损,但没有对冲风险的工具。于是这些精明者积极鼓动金融机构以这个高风险的基础资产设计债券衍生产品。如果正常使用,是可以套期保值、管理风险的。问题是,房地产市场的疯狂、次级贷款市场的疯狂,导致次级贷款债券信用违约互换这个新产品已经不是被持有者用来管理风险,而是成为进行疯狂投机的赌注。据统计,危机爆发前,美国信用违约互换市场的规模最高超过50万亿美元。仅仅美国国际集团一家就持有2.7万亿美元的衍生品合约,它通过高盛等投行卖出的次级贷款债券信用违约互换占了其中的大多数。《大空头》中写道,“以高盛为首的华尔街公司要求美国国际集团承保的消费者贷款包中,包含了大量的次级抵押贷款,其比例从2%变为95%”,终端需求者就是《大空头》主角巴里等一群对房地产次级贷款看空的做空者。他们认为美国的房地产泡沫不可持续,因此拼命寻找抵押贷款池里最坏的债券资产,然后从高盛、美国银行、德意志银行手中大量购买保险——次级贷款债券信用违约互换,他们以建在山顶房子的洪灾保险价格购买了建在山谷里的房子的洪灾保险(不负责任的评级公司留下的漏洞),无情地做空次级抵押贷款债券。
用《泥鸽靶》作者的话说,这类基于质量低劣的基础资产设计的场外衍生品只不过是“在霉变的蛋糕上涂了一层新鲜奶油”。雷曼就跌倒在这种“涂了奶油”的“霉变蛋糕”上,跌倒时手头还有不少这类“蛋糕”。做“蛋糕”的多种原材料从哪里来,霉坏了多久,因为经过多次“设计和生产”,已经没有人能够说得清楚,后面究竟有多大的风险也没有人能道得明白。一旦金融市场恐慌,危机来临,流动性收紧,金融机构谁也不往市场投钱了。雷曼要出售“蛋糕”已经无人接货了,也无人愿意给它融资,“烂货”砸在自己手里,挺不住的雷曼轰然倒塌了。
雷曼的破产,在场外衍生品市场波及了不少无辜的人,但在场内的期货市场上,雷曼的交易对手方却躲过一劫。2008年底,梅拉梅德在北京告诉我,雷曼在芝加哥商业交易所的12亿美元权益没有违约,雷曼的交易对手方都拿回了自己的钱。他说,这主要得益于期货交易的中央对手方清算制度。期货市场由于透明度高、监管严格及中央对手方清算机制,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未受到太大影响。因此,2009年,二十国集团(G20)匹兹堡首脑峰会高度评价期货交易机制,并要求在场外衍生品市场监管改革中借鉴和推广。
由于场内衍生品市场受到严格监管,交易对手获得了与场外衍生品市场不同的命运。
往事千年:期权全球遍地开花
这是一个泰利斯“期权”遍布全球的故事。
泰利斯“期权”穿越2000多年的历史,成为今天金融衍生品的源头。衍生品很古老,但现在它仍然是一个比较活跃的“年轻人”。按照一些研究者的说法,近、现代衍生品存在的时间比较短,近代的衍生品仅仅有100多年的时间,如场内的期货、期权等;而现代的金融衍生品存在的时间更短,不过40年,如场外市场的利率期权、货币互换等。
古希腊的泰利斯“期权”,到了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在威尼斯商人和银行家的商业活动中得到了广泛运用。以古希腊、古罗马文明为基础的西方,在19世纪、20世纪发扬光大了泰利斯精神,继续在金融衍生品领域开疆拓土。19世纪中期,期货合约的出现和期货交易所的建立是一个重大发明。历史上,美国以农产品期货见长,英国以有色金属期货露脸,它们都是在商品远期合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中又以美国期货市场最为典型。美国期货市场的农产品、能源、贵金属期货的价格发现和套期保值功能,对全球的经济活动产生了积极的重要影响。20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在世界上首先开发上市了外汇、利率、股票指数等金融期货,满足了市场主体管理金融风险的需要。最近十多年里,随着新经济的出现,美国、欧盟又上市了碳排放权期货、比特币期货等。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的期货市场也在最近20多年里得到迅速发展,目前中国商品期货市场的交易规模已经连续多年跃居世界前列。
20世纪80年代产生的以金融工程为特征的场外金融衍生品市场是又一大创新。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场内衍生品市场在金融期货的推动下创新很多,发展很快,交易量呈现几何级数的增长。但到20世纪90年代末期,场外衍生品市场发展迅速,很快超过场内衍生品市场。2017年底,全球场外衍生品市场名义本金532万亿美元,总市值  11万亿美元;场内衍生品市场持仓额81万亿美元。
11万亿美元;场内衍生品市场持仓额81万亿美元。 
如今,无论是以商品资产为标的物的大豆、玉米、铜、原油等衍生品,还是以金融资产为标的物的股票、股票指数、国债、利率、外汇等衍生品,无论是场内市场,还是场外市场,现代金融衍生品在世界上已经被很广泛地运用了。
从交易场所看。交易所市场交易的是期货期权合约,是标准化合约,其特点是流动性好、透明度高及竞争性定价、监管严格。场外衍生品市场交易的是非标准化的交易对手双方签订的协议,其特点是个性化,较灵活,但流动性差、不透明、监管松。两个市场有区别也有联系。二者共同的是,它们交易的都是在未来约定时间内必须履行交割的资产或权利;不同的是,交易所平台是所有交易参与者交易标准化的合约,而场外市场是交易者之间“一对一”交易非标准化的合约。它们的联系是,期货交易所市场的存在,使场外市场交易者暴露的风险头寸,可以到场内市场进行对冲管理风险,推动了场外市场的发展。而有风险管理需求的场外市场交易者越来越多地参与场内市场交易,又反过来增加了场内市场的深度、厚度与流动性。二者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壮大。国际金融市场的无数案例说明,许多金融机构在场外衍生品市场的风险敞口,仅仅依靠场外市场的对手方是消化不了的,需要到期货交易所进行对冲。而场内市场的标准化合约和买空卖空交易机制,集聚了大量的市场流动性,可以方便地实现实体企业和金融机构套期保值、风险管理的需要。
从产品类型看。金融衍生品包括远期、期货、期权和互换4种产品类型。如前所述,它们是基于基础资产之上设计的协议或合约。基础资产包括实物商品、金融资产等,如铜、原油、大豆、小麦、棉花、黄金、白银、股票、利率、外汇、指数、信用等。
期货是金融衍生品中最基础、最简单的产品。它和远期、期权、互换等其他衍生品有许多共同之处,但也存在一些区别。
期货与远期的区别。期货是从现货远期交易发展而来的,但二者之间有很多不同之处,可从以下三方面来看。一是,期货是由交易所设计的以某一资产为标的的标准化合约,合约标的资产的品质、交易规模、交割日期都由交易所统一规定,唯一不确定的是价格;远期合约则是由买卖双方通过“一对一”协商达成的,是为了满足双方要求指定的某一资产的非标准化合约。二是,期货在交易所场内进行集中买卖;远期合约在场外市场“一对一”交易。三是,期货交易实行严格的保证金制度,期货交易所为买卖双方提供信用,进行中央对手方清算,市场参与者只承担价格波动的风险,不承担信用风险;远期合约交易不仅承担价格波动风险,还承担信用风险。
期货与期权的区别。两者的区别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在期货交易中,买卖双方的风险和收益都不确定,随标的资产价格变化而变化,且一方盈利总是等于另一方的亏损。在期权交易中,买方的最大风险是确定的,最大损失即付出的权利金,但收益不确定,买方的收益随标的资产价格的变化而变化;期权卖方的风险不确定,损失随标的资产的价格变化而变化,但最大收益是确定的,即为收取的权利金。二是,期货买卖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对等,期货合约到期自动交割,买卖双方都要承担交割义务。而期权买方只有权利,没有义务,既可以选择行权,也可以选择不行权;而期权卖方只有义务,没有权利,被行权指派到就必须履行义务。三是,在期货交易中,交易双方地位对等,都要缴纳一定比例的保证金。期权交易则不然,由于期权权利方不承担义务,所以不需要缴纳保证金,而期权义务方有履约义务,必须缴纳保证金作为履约保证。四是,期货合约本身无价值,只是跟踪价格。而期权合约类似保险合同,合约本身有价值,体现为权利金。期权的风险收益具有独特的非线性特征,在场内和场外衍生品交易中都有非常广泛的应用。
期货与互换的区别。互换指的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当事人在将来交换一系列现金流的协议,远期可以被看作互换最简单的情形。与期货交易相比,互换交易的透明度、流动性都偏低,但在满足客户个性化需求方面具有显著优势,可以对合约标的、数量、到期日、支付频率等做出个性化设计。由于互换使用起来非常灵活,目前已经是场外衍生品市场中规模最大的产品类型。互换交易中,最常见的有利率互换(interest rate swap)、货币互换(currency swap)、收益互换(total return swap)、信用违约互换等。
温馨提示:投资有风险,选择需谨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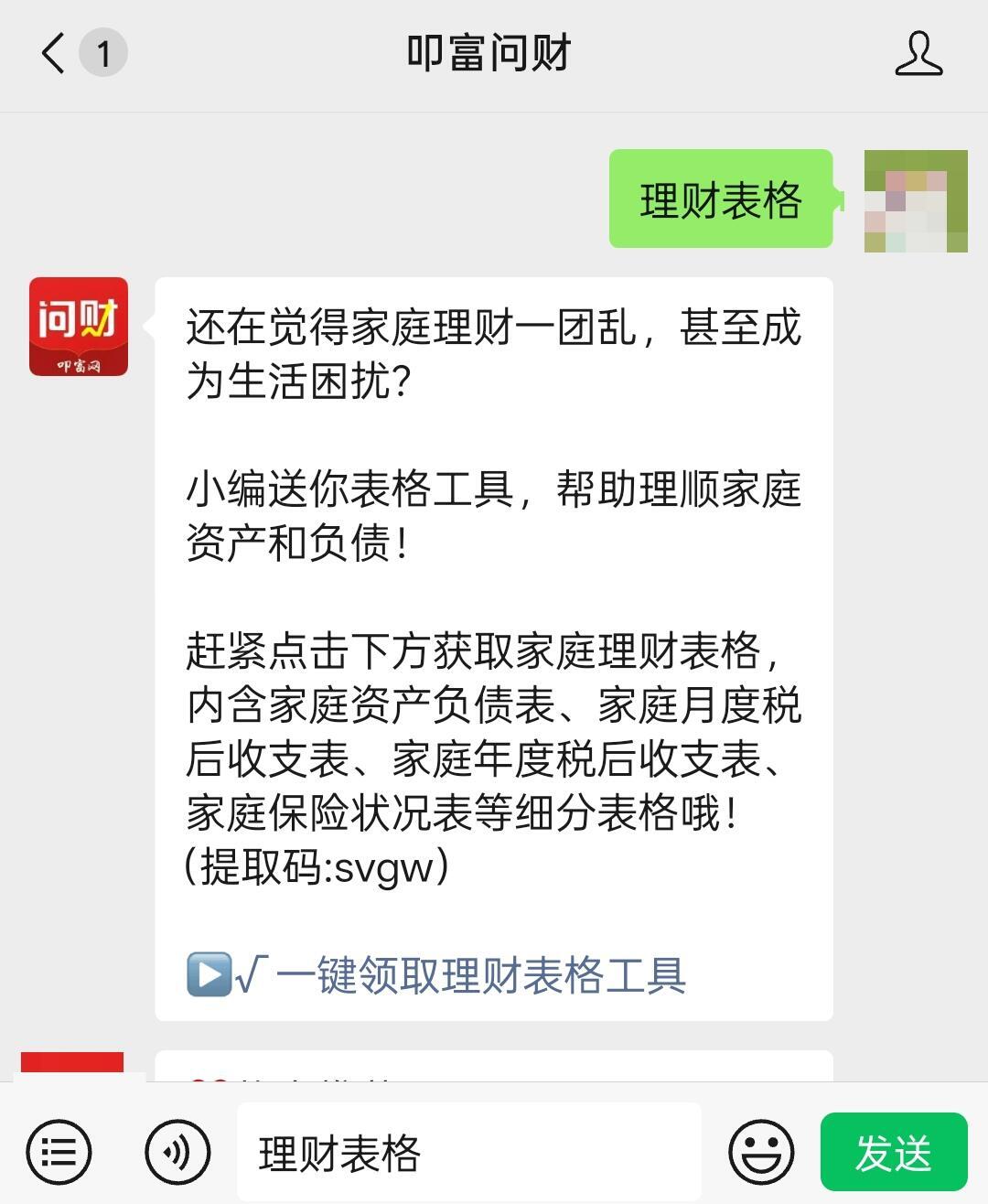


 问一问
问一问
 +微信
+微信
 分享该文章
分享该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