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磨一剑:期货和衍生品法的“前世今生”
发布时间:2022-4-25 16:29阅读:205
“在中国立法史上,少有哪一部法律像期货和衍生品法起草这般曲折和反复,也少有哪一部法律像期货和衍生品法审议这般坚定且迅速。我想这与期货和衍生品本身特点、与期货和衍生品市场发育程度、与市场经济发展阶段、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所处环境密不可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尹中卿在接受期货日报记者独家专访时说。
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滚滚洪流,1990年,郑州粮食批发市场开业,拉开了中国期货市场发展的序幕。三十多年来,中国期货市场从无到小、从小到大,由乱到治、由弱到强,走出了一条极为不平凡的发展之路。
与此相适应,中国期货市场立法工作也从1993年起步,至今已近三十年。
三十年间,立法机关对期货市场格外关注,但立法过程却步履蹒跚、踉踉跄跄。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曾经将期货交易法列入立法规划一类项目,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又将该法列入立法规划二类项目。
此间,起草单位正式形成过三次草稿。八届全国人大财经委曾成立起草领导小组,由董辅礽任组长,1994年8月形成草稿;十届全国人大财经委又成立起草领导小组,由周正庆任组长,2007年6月形成草稿;十二届全国人大财经委再成立起草领导小组,由尹中卿任组长,2015年6月形成草稿,2017年11月提请十二届全国人大财经委第68次全体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期货法(草案)》。
至此,“草稿”终于走出起草领导小组,成为正式“草案”,一字之差,已过二十四载。起草工作之艰难,可见一斑。
与之形成强烈反差的是,期货和衍生品法草案审议过程却出人预料的迅速。2021年4月26日提请并于28日进行初次审议,同年10月19日进行第二次审议,2022年4月18日进行第三次审议并于4月20日表决通过,前后不到一年时间。
“在新中国立法史上,少有哪一部法律像期货和衍生品法起草这般曲折和反复,也少有哪一部法律像期货和衍生品法审议这般坚定且迅速。我想这与期货和衍生品本身特点、与期货和衍生品市场发育程度、与市场经济发展阶段、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所处环境密不可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尹中卿在接受期货日报记者采访时说。
尹中卿认为,如果将金融市场比作市场经济的“皇冠”,期货和衍生品市场就是皇冠上的“明珠”。市场经济发展不到一定程度,衍生品市场发育不够成熟,期货和衍生品市场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遑论立法。回顾历史可以看出,期货和衍生品立法,以我国期货和衍生品市场发育程度为条件,以市场经济发展阶段为支撑,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所处大环境为基础。
回顾期货和衍生品法的“前世今生”,尹中卿感慨万千。他强调,“这是期货和衍生品行业和市场及关心期货和衍生品的各界人士共同书写的一页历史。三十年立法之路虽然艰辛,却终有所获!”
“三十年立法之路,有党中央的决策部署,有几代立法者的辛勤努力,有相关主管部门的开放包容,有行业从业人员的默默耕耘,有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期货和衍生品法的颁布实施,是全社会集体智慧的结晶,每一步艰难前行,都源于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尹中卿说。
清理整顿时期的一草稿
1993年,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将“期货交易法”列入立法规划一类项目,全国人大财经委成立起草领导小组,组长由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董辅礽担任。
中国期货立法,拉开大幕。
董辅礽先生是中国著名经济学家,他在理论和实践上为推动中国市场经济改革与经济发展做出过重大开拓性的贡献,在学术上取得了多方面的丰硕成果。他曾提出,期货市场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在董辅礽的主持下,起草领导小组在1994年8月形成“期货交易法”草稿(下称一草稿)。1995年9月,董辅礽在上海公开表示,法制建设是目前期货界最为迫切的任务,只有在法规中加以明确,才能规范期货市场各方参与者的行为,包括政府行为。

彼时,中国期货市场在经过初创期后,交易场所建设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截至1993年年底,冠以“商品交易所”“期货交易所”字样的期货市场,全国已有33家,最多时达到50多家。这也为期货市场的后续发展埋下隐患:交易场所数量过多,品种重复上市,过度投机严重,市场操纵频发;期货经纪公司运作不规范,地下交易、境外期货交易集中引发了一系列经济纠纷和社会问题。
1993年11月4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坚决制止期货市场盲目发展的通知》,标志着中国期货市场步入清理整顿阶段。
1993年之后,一草稿虽然数易其稿,但无奈“生不逢时”。在期货市场存续尚且存疑的清理整顿阶段,人们对发展期货市场的意见分歧很大,立法工作也陷入了停滞状态。
回头来看,八届全国人大对制定期货交易法非常重视,也很有信心,这是迄今唯一将其列入立法规划一类项目的一届全国人大,也是第一届将其列入立法规划的全国人大,是我国期货立法工作的起点。
立法规划是每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工作的“任务表”“施工图”。一类项目,即条件比较成熟的立法项目。二类项目,即需要抓紧工作、条件成熟时提请审议的立法项目。三类项目,则是条件尚不完全具备,需要继续研究论证;经研究论证,条件成熟时,可以安排审议的立法项目。
据尹中卿介绍,全国人大代表涉及期货立法的议案,可以追溯到1994年。在八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张仲礼(时任上海社会科学院院长、著名经济学家)等30位代表、彭复生(时任中国民主促进会重庆市副主委兼秘书长)等32位代表、李崇淮(时任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副主席、武汉大学教授、著名经济学家)等32位代表,分别提出了要求加快期货立法的议案。这3份议案,称得上关于中国期货立法的“一号议案”。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加之期货市场清理整顿尚未结束,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未将期货立法列入立法规划。
规范发展时期的二草稿
1999年6月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267号发布《期货交易管理暂行条例》,标志着中国期货市场步入规范发展阶段。
2001年12月11日,中国经历多年谈判终于拿到WTO(世界贸易组织)“入场券”。
中国期货市场再次迎来立法契机。
2003年,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将“期货交易法”列入立法规划二类项目,全国人大财经委成立起草领导小组,组长由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周正庆担任。
在赴全国人大工作之前,周正庆曾担任中国证监会主席。任期内,他整顿了场外非法股票、期货、基金等交易市场,主导了中国股市著名的“5·19”行情。
在周正庆的主持下,起草领导小组在2007年6月形成“期货交易法”草稿(下称二草稿)。
2007年8月,周正庆在大连公开表示,目前金融期货还未正式推出,而金融期货在我国将会如何运行,以及会出现哪些问题,都是未知数。待金融期货正式推出并运行一段时间后,起草领导小组将根据金融期货实际运行特征,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对二草稿进一步完善、修订后,再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2007年12月3日,周正庆在深圳公开表示,期货交易法是一部全面规范期货交易各个方面关系的法律。
他介绍说,二草稿对期货交易所、期货公司、期货投资者、其他期货服务机构、期货业协会管理、监督权利义务关系分别进行了规定。同时对一般性的规则,结算、交割、信息披露以及禁止的行为、境外期货业务等分别做了规定。在法律责任方面,为了保证期货交易的规范,侧重系统风险的布置,二草稿也做了较为详细的规定。
彼时,中国期货市场和衍生品市场形成了以《期货交易管理条例》为核心,以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为支撑,相关行业协会、交易场所自律规则为补充的法规制度体系。期货和衍生品品种数量不断增多,市场成交量屡创新高,但不可否认的是,金融期货尚未起步,期权等衍生品、市场对外开放等重大创新仍在研究,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给当时起草工作带来不利影响。
雪上加霜的是,虽然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2006年9月8日就已成立,我国第一个金融期货品种——沪深300股指期货合约却直到2010年4月16日才挂牌上市。
此间,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将“期货法”列入立法规划二类项目,但并未开展任何实质性工作。
期货和衍生品立法的主要难点和争论点
在期货和衍生品立法过程中,经历了很多不同观点主张的激烈交锋,草案也数易其稿,几经修改。尹中卿告诉期货日报记者,在立法过程中,起草组始终站在中立位置,公允地协调各方分歧和争论,在矛盾焦点处“砍一刀”,竭力避免部门色彩,最大程度凝聚共识。
在尹中卿看来,期货和衍生品法立法遇到的第一个难点和争论点,就是期货和衍生品市场功能定位理论准备不足,没有形成社会共识。期货和衍生品市场的突出特点是专业、复杂、小众,虽然参与人不多,但是对国计民生、经济运行、市场秩序的影响却很大,很多人对其缺乏了解。这些年境内外出现的某些风险事件,更是加深了一些人对期货和衍生品市场的误解。这也是此前的一草稿和二草稿未能进入审议程序的重要原因。
“在起草过程中,我们的首要工作是凝聚共识,明确期货和衍生品市场发现价格、管理风险、配置资源的基本功能,强化期货和衍生品市场服务国家战略、服务实体经济的重要意义。”尹中卿说。
立法过程中遇到的第二个难点和争论点,是期货之外的其它衍生品是否应纳入此次立法法律的调整范围?
一种意见认为,期货是小概念,衍生品是大概念。衍生品既包括期货即商品类衍生品,也包括金融类衍生品;既有在交易所通过集中竞价交易的场内衍生品,也有通过一对一询价、协商、撮合交易的场外衍生品。我国期货与衍生品市场发展程度不一,期货市场已经稳定运行多年,监管制度比较成熟,而衍生品市场尚处于探索发展阶段,在法律里统一规定可能会限制衍生品市场发展,最好等待条件成熟时再单独立法。
另一种意见认为,期货交易与衍生品交易没有本质区别,市场法律性质、基本属性总体相同。期货市场适用的法律关系、监管逻辑很多可借鉴于衍生品市场。目前我国还没有关于场外衍生品的法律和行政法规。2019年我国修订证券法,删除了有关证券衍生品的规定,留给期货法。期货和衍生品最好纳入同一部法律中。
“我们衡量再三,不管有多少不同意见,还是采取综合立法模式,坚持把期货和衍生品纳入统一调整范围,将制定的法律定位为广义法,而不是狭义法,适应金融市场从行业监管转变为功能监管、从机构监管转变为行为合规监管的趋势,避免各自为政,造成监管空白。”尹中卿说。
在初次审议之后,将法律名称从《期货法(草案)》更名为《期货和衍生品法(草案)》,明确了以期货为主、兼顾衍生品,以场内为主、兼顾场外,以标准化产品为主、兼顾非标准化产品,以境内为主、兼顾境外的原则。
立法过程中遇到的第三个主要难点和争论点,是期货和衍生品法的监管体制,主要涉及草案一审稿和二审稿第七条的内容。
尹中卿回忆说,虽然第七条只有两款,总共三层规定,但是在起草和审议过程中,却经过了多次修改。草案一审稿第七条规定,“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依法对全国期货市场实行集中统一监督管理。利率、汇率期货由国务院依法另行规定。”“其他衍生品市场由国务院授权的部门实行监督管理。”
草案二审稿第七条改为,“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依法对全国期货市场实行集中统一监督管理。国务院对利率、汇率期货的监督管理另有规定的,适用其规定。”“衍生品市场由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或者国务院授权的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实行监督管理。”
尹中卿解释,“就第一款来说,一审稿实际上将利率和汇率期货拿出来,由国务院另行规定的部门实行监督管理。二审稿进一步加强了集中统一监管,如果国务院对利率和汇率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如果没有规定,均由期货监督管理机构实行集中统一监管。”
“就第二款来说,一审稿明确期货之外的其他衍生品市场由国务院授权的部门实行监督管理,二审稿在国务院授权的部门之前,增加了期货监督管理机构,要求两者按照职责分工实行监督管理。”“总体上看,二审稿第七条两款的修改,都更加重视国务院期货监管机构集中统一监管职能。此内容在三审稿调整为第八条。”
立法过程中遇到的第四个主要难点和争论点,是对服务机构的监督管理问题。草案一审稿规定,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产品质量检验机构、信息技术服务机构等从事期货服务业务,需要向期货监管机构和有关主管部门备案,这就导致上述机构在已有主管部门的情况下,还要接受双重管理。按照“放管服”改革精神,草案二审稿对此进行修改,除信息技术服务机构外,删除了其他服务机构的备案要求,有利于减轻相关服务机构的负担。
“事实上,立法过程中遇到的难点和争论点还有很多,有些甚至到如今也未达成共识。我们始终把握的原则是,在实践中不成熟的问题、争论过于激烈的内容,先不要规定到法律里面,避免影响法律的顺利出台,避免引起歧义影响法律实施效果。”尹中卿说。
尹中卿强调,虽然立法过程中存在各种各样的难点和争论点,但此间各方的包容性、开放性以及取得共识的过程,更令人记忆犹新。
来自:期货日报
温馨提示:投资有风险,选择需谨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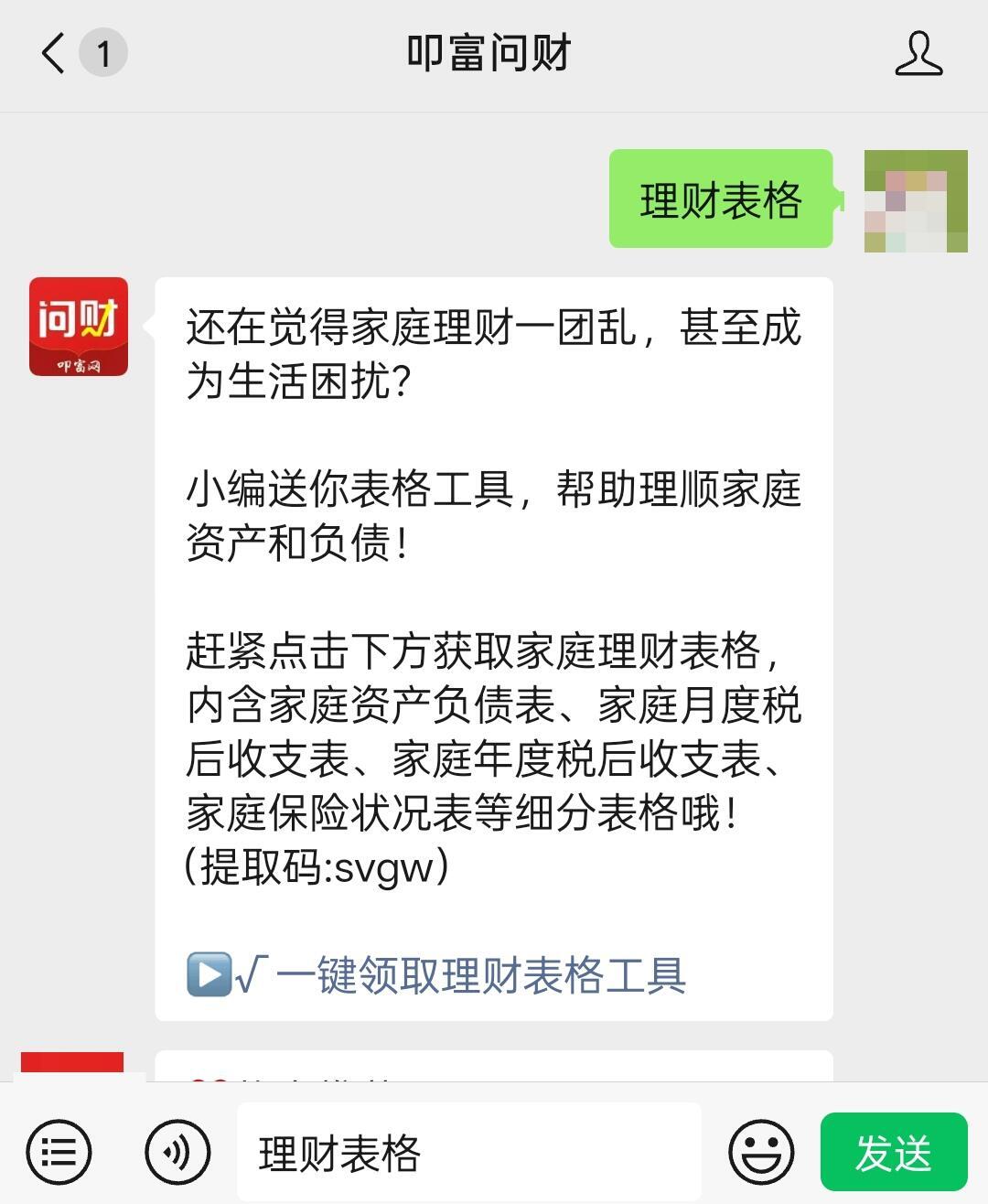



 问一问
问一问
 +微信
+微信
 分享该文章
分享该文章












